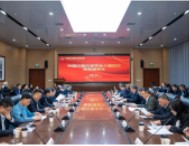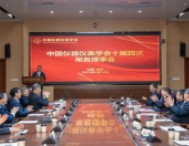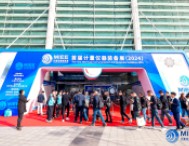作者簡介:

譚久彬
中國工程院院士,精密測量與儀器工程專家,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儀器科學與技術學科教授、博導,精密儀器工程研究院院長,超精密儀器及智能化工信部重點實驗室主任。兼任國家計量戰(zhàn)略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際測量與儀器委員會(ICMI)常務委員、中國儀器儀表學會副理事長等。
正文:
高端裝備雄踞制造業(yè)技術鏈和價值鏈的頂端,其最本質的特征是高質量,包括高性能、高穩(wěn)定性和高可靠性。中國裝備制造要實現(xiàn)突破,首先要解決制造質量問題,其關鍵是能否建立起堅實的技術基礎支撐能力,而核心關鍵是能否首先建立起超精密測量能力。沒有超精密測量,就不會有高質量的高端裝備制造。我國需要加速實施“測量三能力”建設,即補齊精密測量能力,追平超精密測量能力,突破和掌握基于“完整精度”的測量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制造與測量兩種能力無法分家,必須實現(xiàn)制造測量一體化,形成有效的精度調控能力。只有構建起系統(tǒng)的精度調控能力,中國裝備才能順利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

跨越百年,德國質量如何大翻身
德國制造已經(jīng)是高質量的象征。但德國并不是天生就有高質量制造的基因,它也經(jīng)歷了從低質量向高質量的轉化過程。在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期間,德國也經(jīng)歷了追趕和大量仿造、質量缺失這樣一個過程。1887年,由于德國低廉產(chǎn)品的競爭,導致英國市場混亂,所以英國議會出臺了一個《商標法》,要把質量低劣的德國產(chǎn)品和高質量的英國產(chǎn)品區(qū)分開。“德國制造”成為一個恥辱性的標志。英國這個法案的出臺使德國朝野震動,舉國反思后得出的結論就是:“沒有精密的測量,就沒有精密的產(chǎn)品”。認識統(tǒng)一之后,德國人馬上行動起來,由西門子出資在柏林建立德國計量院,這個計量院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計量院。以它為統(tǒng)領,逐漸構建起了德國國家測量體系,即從國家計量基準/標準的建立、管理與量值傳遞,把準確的量值傳遞到車間里面,一直到貫穿到制造過程的每一道工序的工程測量。這種國家測量體系,確保了測量數(shù)據(jù)的準確可靠,進而保證零部件制造精度和產(chǎn)品集成后的精度與質量。由于有了以國家計量院為統(tǒng)領和以健全而強大的現(xiàn)代工業(yè)測量體系為根基的國家測量體系作為支撐,德國的產(chǎn)品質量迅速提升。
第二次工業(yè)革命期間,德國已經(jīng)具備了整體精密工程能力,全面實施質量戰(zhàn)略,使得德國制造業(yè)迅速崛起。這期間德國生產(chǎn)出來以精密坐標測量機為代表的一批精密測量儀器與制造裝備,建立起了完整的精密測量體系,對高端裝備制造形成強有力的支撐。
第三次工業(yè)革命時期,德國率先進入了超精密工程階段,并率先形成整體超精密工程能力。不斷升級和完善質量戰(zhàn)略,使質量意識深入人心,國家測量體系成熟高效,使德國成為名副其實的質量強國,形成了一大批自己的品牌。這期間它培育起了一批頂尖超精密制造與儀器企業(yè),建立了完整的超精密測量體系。盡管德國工業(yè)規(guī)模不算很大,但卻擁有世界品牌2300多個。
這一時期,超精密制造和超精密測量能力支撐了以光刻機為代表的高端超精密裝備的快速發(fā)展。荷蘭ASML公司異軍突起,超越了日本的尼康和佳能,成為超精密光刻機制造的佼佼者。但是,荷蘭ASML公司并不生產(chǎn)核心零部件,它主要從事設計、研發(fā)、組裝、整機調試和售后服務等,而絕大部分的核心零部件如光學鏡頭等都生產(chǎn)于德國等高端制造業(yè)發(fā)達國家。換言之,荷蘭ASML公司的光刻機,是建立在德國等國家的超精密制造與測量能力上的。
到了第四次工業(yè)革命期間,德國人率先提出了工業(yè)4.0的概念。從德國的發(fā)展歷程可以知道,德國是從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以后穩(wěn)扎穩(wěn)打,循序漸進,扎扎實實地解決了產(chǎn)品的質量問題,然后再穩(wěn)步進入智能制造階段。

中國測量能力的發(fā)展歷程
中國制造在改革開放前,初步形成了裝備制造能力,而且在某些點上邁向了精密工程,在局部形成了精密測量能力,如九大裝備中的萬噸水壓機,個別零件就是精密級的,而且這些精密級零件,必須要通過精密測量才能保證質量。中國在個別產(chǎn)品、個別部件上探索了精密級的制造和測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