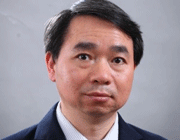金國藩:光存儲一度非常熱,以前計算機都配有光盤驅動,現在都沒有了。原來光盤有存儲容量大的特點,可是遇上圖像就需要壓縮和解碼,傳輸速度不理想。現在看,一張光盤的容量還不到一個Gb,而1Tb的U盤都有了。
體全息存儲技術基于 “頁面” 方式對圖像并行處理,訪問速度極快,存儲量巨大。一個10 mm3的鈮酸鋰晶體可存儲1萬幅以上圖像,對幾個Gbytes容量的存儲器訪問時間僅為幾毫秒,圖像可即時查看。還有,不必經過計算機就能直接與圖像傳輸系統對接、存儲,如衛星偵察圖像系統。
計算機數字圖像處理靈活性大,但逐行掃描,速度慢; 體全息存儲容量大,尋址方便,信息存儲極快,可利用它作內積相乘,解決圖像識別問題。因此,我們研制了光電結合的體全息相關器,預處理由計算機完成,識別由光計算來實現,這樣可兼備兩種處理的優越性,作到既快速,又保證高精度。
現在數字技術比光學技術發展得快,所以人們都用U盤。可是磁盤要想長時間保存的話,過幾年就得刷新一下。從這個角度說,我覺得光盤還是有希望的,因為它存儲時間比較長。
最近有人在研究30層的三維光存儲技術。我覺得如果真能做30層的話,一層一層地疊加,里面很可能有雜質或者氣泡摻雜進去,不太容易做好。如果從存儲的時間長度考慮,還是有意義的。不過不太可能成為個人電腦的一部分。
張志剛:您如何看中國制造的光學儀器呢?現在光學精密儀器進口的還是很多,您覺得是什么原因?
金國藩:我曾經跟科技部提過,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國產器件的穩定性、可靠性比較差。國內做出了某個儀器,但是大家還是都愿意買國外的,為什么呢?因為國外的儀器穩定性好,使用很多年都沒有問題,國內的儀器可能剛開始獲取的數據還可以,但后期的穩定性就不太好。
另外,我覺得科技部可能太重視產業化。課題設置沒有充分考慮到科技的發展前景,缺乏研究工作,到頭來90%的項目牽頭人都是企業,我覺得這是不合適的。想法雖然是好的,但是企業一天到晚考慮的是生存,是賺錢,很少考慮科技前景。企業牽頭,心態上只當項目做,花完錢完事,這樣就不能持續創新。與此相反,基金委又太重視前沿。只注重研究成果,較少關心成果轉化,所以,成果落不了地。我覺得這兩個方面各有各的問題。
張志剛:您能介紹一下清華主導成功制造了哪些光學儀器嗎?
金國藩:對于清華主導制造的光學儀器,雖然可以說是成功的例子,也可以說是不成功的例子:就是剛才說的中國第一臺三座標光柵測量機。現在這個技術已經陳舊了。
我們研究過光刻機技術。我們可能是國內做的最早、也是最多的,大概做了有100多臺光刻機吧,當然與國外相比差距很大。可惜后來也不做了。
張志剛:聽說您在中國加入國際光學委員會(ICO)這件事上起了很大作用,能說說具體過程嗎?
金國藩:國際光學委員會(ICO)是聯絡各國光學學會的一個組織,1947年成立。我在德國進修時認識的羅曼教授,恰是當年的ICO主席。有一天他跟我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從事光學科學與工程的人很多,中國光學學會應該參加ICO”。中國還不是ICO的會員?我回國后趕緊向中國光學學會理事長王大珩先生匯報了這件事。王先生召集中國光學學會常務理事開會,會上大家都同意參加ICO,我就給羅曼教授寫信說中國要參加ICO。
哪知道臺灣方面的“光學工程學會”已經在ICO里了。根據我國科協的政策,在國際組織中不能出現兩個中國。這給ICO出了個難題。當時我負責中國光學學會的外事工作,不知給下一屆ICO主席石內順平寫了多少封信,也不知石內順平做了多少工作。最后臺灣方面同意采用奧運模式,改叫“光學工程學會(臺北)”,才解決了這個問題。1987年ICO通過了中國光學學會作為正式會員。母國光院士被選為1993-1999年ICO副主席,我被選為2002-2008年ICO副主席。
張志剛:后來您還做了哪些促進中國和世界光學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