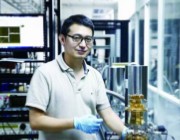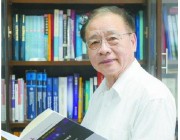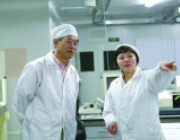中國(guó)科學(xué)院和中國(guó)工程院外籍院士,對(duì)于促進(jìn)中國(guó)的科技進(jìn)步做出了什么貢獻(xiàn)?
澳大利亞科學(xué)院院士、澳大利亞技術(shù)科學(xué)與工程院院士、澳大利亞聯(lián)邦研究委員會(huì)桂冠教授和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xué)副校長(zhǎng),中國(guó)工程院外籍院士顧敏,從小在青浦區(qū)朱家角長(zhǎng)大的顧敏,1982年畢業(yè)于上海交通大學(xué)應(yīng)用物理系,1988年獲得中科院上海光機(jī)所光學(xué)博士學(xué)位。“我在上海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我文化的根就在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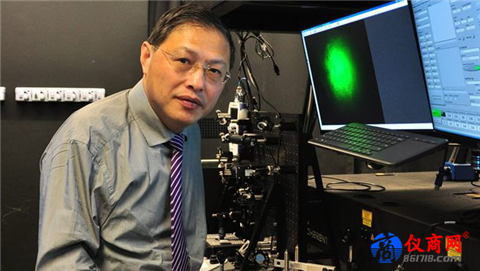
一張DVD的存儲(chǔ)量相當(dāng)于1萬多張
“聽說過燒刻光盤嗎?這實(shí)際上是在光盤里打了一個(gè)個(gè)的‘坑’。”顧敏向記者娓娓道來他研究的光存儲(chǔ)技術(shù)。日常生活中的DVD和CD光盤要想存儲(chǔ)更多的音樂和圖像,需要在光盤上打出一個(gè)個(gè)“坑”,用光來儲(chǔ)存信息,這就是燒刻。要想把光吸收的能量最大化,就要在一個(gè)“坑”里盡可能放更多的“點(diǎn)”,同時(shí)這個(gè)“點(diǎn)”越小越好。藍(lán)光的光點(diǎn)比紅光的光點(diǎn)儲(chǔ)存的信息更小,因此出現(xiàn)了藍(lán)光儲(chǔ)存技術(shù)。顧敏首次在納米材料中實(shí)現(xiàn)了五維光存儲(chǔ),突破了藍(lán)光DVD三維存儲(chǔ)的技術(shù)瓶頸,他發(fā)明的雙光束超分辨存儲(chǔ)技術(shù),使得一張DVD的存儲(chǔ)量可相當(dāng)于1萬張DVD的存儲(chǔ)量。這一成果在2009年,以封面形式刊載在了國(guó)際權(quán)威科研期刊《自然》上。
“目前全世界3%的能量被用于大數(shù)據(jù)儲(chǔ)存,再過20年,數(shù)據(jù)越來越多,把全世界開發(fā)的石油用來發(fā)電都不夠。”顧敏介紹,現(xiàn)在的大數(shù)據(jù)一般用磁盤存儲(chǔ),這種存儲(chǔ)方式讀寫速度快,但消耗能量大,一般只有三五年壽命,需要重新存儲(chǔ)。因此,顧敏在2013年發(fā)明了雙光束超分辨存儲(chǔ)技術(shù)。使用這一技術(shù)的光盤,不僅容量大,且單點(diǎn)消耗的能量非常低,使用壽命可以達(dá)到上百年。這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具有非常實(shí)用的意義。
作為公認(rèn)的三維光學(xué)成像理論的國(guó)際權(quán)威和先驅(qū)者之一,顧敏對(duì)現(xiàn)代光學(xué)顯微成像術(shù)的發(fā)展有重要推動(dòng)作用。他是雙光子熒光共焦顯微學(xué)的發(fā)明者之一,該技術(shù)被生物學(xué)界視為非常重要的高空間分辨顯微技術(shù)。顧敏在《科學(xué)》《自然》《自然光子學(xué)》等國(guó)際權(quán)威期刊發(fā)表了超過450篇論文。
推動(dòng)了中國(guó)生物光子學(xué)和納米光子學(xué)發(fā)展
“我是看著上理工新的光電大樓造起來的!”顧敏笑著說起了他和上海理工大學(xué)的合作。早在上海交通大學(xué)讀書時(shí),顧敏就讀過莊松林院士的論文,對(duì)這位前輩仰慕已久。2008年,顧敏回上海探親,參觀了上理工的光學(xué)實(shí)驗(yàn)室,就此促成了他們之間的第一次合作,首次在光學(xué)波段實(shí)現(xiàn)了反多普勒效應(yīng),并在《自然》子刊聯(lián)合發(fā)表論文。
太赫茲是一種有很多獨(dú)特優(yōu)點(diǎn)的輻射源,可用于檢測(cè)食品安全、藥品、危險(xiǎn)品和爆炸物等。顧敏每次在上海的行程都排得很滿。
除此之外,顧敏還想在上海推進(jìn)“三維立體顯示器”項(xiàng)目。目前的三維立體顯示器,名為三維,但實(shí)際只有10度的視角,還需戴眼鏡。顧敏團(tuán)隊(duì)現(xiàn)在可以做到50度的視角效果,接下來他希望可以做到不戴眼鏡,顯示器的厚度只有頭發(fā)絲的千分之一。
多年來,顧敏致力于推動(dòng)中國(guó)光科技發(fā)展以及中澳之間的科技合作,卓有成效地推動(dòng)了中國(guó)生物光子學(xué)和納米光子學(xué)的成長(zhǎng)和發(fā)展。他先后入選教育部長(zhǎng)江學(xué)者講座教授、中國(guó)科學(xué)院愛因斯坦講席教授和首批國(guó)家(B)。
既要抓基礎(chǔ)研究和原創(chuàng)發(fā)明,也要重視產(chǎn)業(yè)化
“我是中國(guó)培養(yǎng)的土博士,對(duì)此我非常自豪。”顧敏給記者講述了他在澳大利亞做博士后的經(jīng)歷。那是1988年,他第一次見到鼠標(biāo),不知道怎么用,被人當(dāng)面嘲笑。當(dāng)時(shí)澳大利亞和美國(guó)的GPS項(xiàng)目合作,需要編程把衛(wèi)星信號(hào)引下來,盡管這和顧敏的專業(yè)沒什么關(guān)系,他卻自告奮勇完成了編程,而且一直用到現(xiàn)在,令人刮目相看。“這正得益于我在中國(guó)所受到的扎實(shí)的基礎(chǔ)教育。”顧敏后來成了第一位華裔澳大利亞科學(xué)院院士。
顧敏是我國(guó)恢復(fù)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屆大學(xué)生,他一直在感嘆受益于這個(gè)大時(shí)代。“我博士畢業(yè)后就出國(guó)了,在澳大利亞培養(yǎng)了50名博士。但我心里一直都牽記著,上海是生我培養(yǎng)我的地方,想要對(duì)上海和中國(guó)做出更大的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