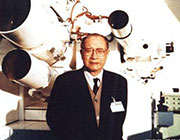教育部直屬院校的高等學校數量,從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候的幾十所,一躍發展到現在2800多所,與成為全球高校數量最多的美國并駕齊驅。而在2800多所高校中,我國擁有光電系或者光電學院的高校約230所,加上研究生,每年光電專業畢業生近四萬人。相比之下,美國只有3所高校擁有獨立的光電學院,每年以光電專業畢業的美國本科生不超過百人。“我國研究生和本科生人數超過了整個歐洲的總和。我們幾乎以一己之力為全球培養了大量的光電后備力量,總量占全球一多半。”
“我剛進入浙大光儀系學習的時候,條件非常艱苦,實驗設備匱乏,最開始的實驗就是磨玻璃。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硬件教學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已經不再是制約人才培養的主要因素了。而國內高校之間的合作和交流甚少,有些甚至壟斷優質生源,成為了人才培養的新問題,這不利于我國光學綜合人才的培養,”劉旭指出,“我國科技水平的發展,最終還是落實到人,必須要打破各高校之間的壁壘,培養高素質高水平人才,為我國光學事業積累堅實的后備力量。”
在歐洲,一項名為“瑪麗·居里國際智力引進行動計劃” (MSCA)享有極高聲譽。它是歐盟針對成員國之外的優秀人才實施的專項資助計劃,旨在通過先進的跨學科、跨領域、跨部門和跨國家的學術訓練,增強科研人員創新能力和創造潛力,支持科研人員學習和轉移新的知識和技能。
了解到這項計劃后,劉旭也希望能夠在中國開展類似的人才培養模式,實現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教學互通。但是他也坦言,MSCA計劃是在歐盟框架協議下執行的,實際操作和執行會比較便利。而我國尚沒有一個指導性協議,也沒有先例,推動困難巨大。“但是這個事得有人去做。”
當劉旭擔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專業教學指導分委員會主任委員、電子信息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時,光電教指分委便召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理工大學、電子科大、華中科技大學、浙江大學、天津大學和長春理工大學等六所高校負責人及五大光機所負責人,共同探討中國的人才培養模式,推進落實。
“從6所主要的光學教育學校中抽出兩屆共48名學生組成‘王大珩班’。每個學期在合作的高校中學習,選修這些學校中最好的專業,最好的老師的課,連續完成4年的大學生活。學習結束后再去各光機所實習。這種資源整合的教學計劃,既可以打破各學校之間的壁壘,為相關領域輸送優秀的后備人才,又可以讓學生獲得最好的教育資源,提升自身本領。”
目前第一批輪值學生已經進入大三階段的學習。下一步,劉旭計劃將“王大珩班”的本科生送到日本濱松學習交流,開展國際間的交流,將這種模式擴展成為文化較為相近的東亞教育圈的人才培養。

第一批“王大珩班”同學于浙大合影(圖中為浙大光電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劉向東(第二排左五))
四、光學學科會長久地存續下去
“光學與其他的工科不一樣,它涉及很強的基礎物理學問題,也涉及太多人類未來的東西,從這一方面來說,光學的任何一個大的突破,都可能會對人類的發展和變革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光學這個學科會長久的存續下去。” 劉旭說道。
誠然,21世紀是光的世紀。智能機器人、手機中的光芯片、傳統制造業中的激光加工、智能醫療診斷、現在的5G,未來的6G等等,都有光技術的身影,并作為主導的傳播媒介。尤其是在疫情肆虐的環境下,數字網絡無疑成為了工作和生活主要工具,即使不出家門,也可無國界交流,即時獲得國內外的海量數據,而這其中光通信技術更是無可替代。還有可折疊時空的量子信息技術,正在開啟新的機遇之門,成為全球信息化戰爭的新戰場。

光子技術的無處不在
圖源: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晝馬輝夫著作《21世紀的光子學》
“這些以光為主要傳輸媒介的技術發展到最后,帶來的變革很可能是具有顛覆性的,會讓我們人類重新審視、認知自己,認知這個世界。這倒讓我想起老晝馬(晝馬輝夫)的那句話:光是物質的膠水,把光發展起來了,你才能真正的認識物質的本質。”
結語
“我們的學生正處在一個很好的時代,經濟快速發展,物質條件富足。作為學生,要打破范式禁錮,擁有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想。因為當你成為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時候,你才能獨立的思考社會應該發展的方向和他應該擁有的社會形態,站在更高的角度,明辨是非,不為各種輿論、利益所誘惑,而真正為著你的人生價值去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