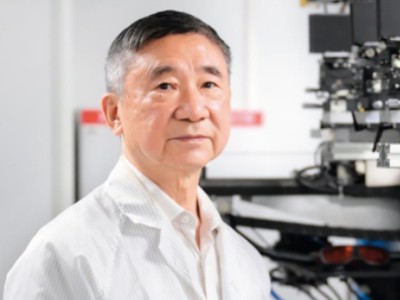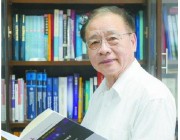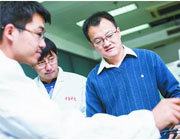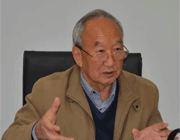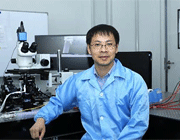四大光機所是我國光學事業的發源地,也是最早的光學體系根基。他們像母親河一樣,源源不斷地向全國各地輸送著光學人才。在四大光機所里,有很多有趣的人和事,正是他們的努力,奠基了我國光學事業的如今蓬勃發展。我們將從祖國的西邊開始探尋。本期,讓我們一起走近中國科學院西光所首任所長龔祖同院士。
我是一個科技工作者,一生求學科研,耳聞目睹,在我心靈中形成這種觀念: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唯有科學技術是建國的大事,不朽的盛業。
——摘自龔祖同1979年1月《入黨志愿書》

1984年8月,龔祖同審查設計方案
西渡東歸:所學所研專業為國所需所用
龔祖同,1904年11月10日生于上海市川沙縣一個小學教師家庭。幼年隨父親上小學常過黃浦江,看到滿江都是外國輪船,心里很難過,總想著哪一天江上的船能飄揚中國國旗。此時的他已在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了科學救國、實業興國的種子。1926年龔祖同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帶著母親以土地作抵押借來的錢和科學救國的強烈愿望邁入清華園。1930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任教。1932年進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師從我國實驗核物理先驅趙忠堯。
1930年,趙忠堯完成實驗的結論震驚了當時的物理界,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觀測到正電子,后來的實驗更讓他成為世界上首次發現反物質的物理學家。
1932年到1934年,龔祖同作為趙忠堯的研究生,對二次γ輻射做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伴隨硬γ射線反常吸收的二次γ輻射的波長》和《趙忠堯、龔祖同致Nature雜志》,對趙忠堯發現伴隨硬γ射線反常吸收的二次γ輻射之后國際學術界在理論上所做的不同推測和解釋做了實驗驗證,并指出Thcγ射線的瑞利散射并不存在。
正當龔祖同在實驗核物理的前沿取得初步成績并滿懷信心開拓前進時,祖國的需要改變了龔祖同的科學生涯。
“九一八”事變后,戰爭的烏云籠罩華北。時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的葉企孫,看到對軍事極為重要的應用光學國內尚屬一片空白,十分焦急。1934年,留美公費考試中恰好有一名應用光學名額,他決定動員刻苦鉆研并初露鋒芒的龔祖同去報考。他對龔祖同說,應用光學在國防上很重要,我國還是空白,留美公費考試中有一個應用光學名額,望能報考。
“是空白,我就去填補。”龔祖同毅然接受了這個決定他一生專業方向的提議,被錄取為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應用光學直讀博士學位的公費生。但后來,導師趙忠堯指出,德國光學在世界上領先,不一定去美國。龔祖同接受了這個建議,于1934年夏,經西伯利亞去德國柏林技術大學(現稱柏林工業大學),開始了他研究應用光學的生涯。
1936年,龔祖同以 “優秀畢業生”的榮譽自該校畢業并獲特準工程師稱號,隨即在應用光學專家F·維多特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工程博士學位的論文工作,題目是“光學系統高級球差的研究”。這項研究的意義在于開始了我國高級像差的研究,并為把光學設計引入我國奠定了基礎。
1937年底,他博士論文完成且行將答辯。這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內要他盡快回國籌建軍用光學儀器工廠。1938年初,他放棄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會,毅然回國,投身抗日戰爭,參加我國第一個光學工廠——昆明兵工署22廠,也稱為昆明光學儀器廠的組建工作,決心為前線將士制造一批雙目望遠鏡。
開創眾多第一:為中國應用光學領域
第一批軍用望遠鏡。龔祖同采用德國的設計技術,使用當時國內僅能找到的一臺電動計算機,很快完成了制造雙目望遠鏡的光學設計的第一關,在克服日本侵略帶來的物質條件上的種種困難后,僅用了半年多時間就制造出了中國第一批軍用雙目望遠鏡,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龔祖同的這項工作不僅實踐了他科學救國的理想,也與當時遷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嚴濟慈、錢臨照等試制顯微鏡的工作一起,開創了中國近代光學設計與光學儀器制造的歷史。
在完成雙目望遠鏡的試制、生產后,他又試制了機槍瞄準鏡,參與試制了倒影測遠機。
第一架紅外夜視儀。1958年,依據新中國的國防安全急需,龔祖同指導研究生王乃弘試制成功中國第一只紅外變像管并制成了中國第一架紅外夜視儀,隨后推廣至云南光學儀器廠,武裝了火炮及重機槍。1960年又試制成功使用多堿陰極的可見光靜電聚焦三級串聯像增強器,用于被動式微光夜視,即一種無需照明、僅依靠微弱的月光及星光觀察的夜視技術。這開創了中國的夜視技術的歷史,為我國微光夜視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8-1960年,龔祖同主持研制成我國第一臺透射式電子顯微鏡。